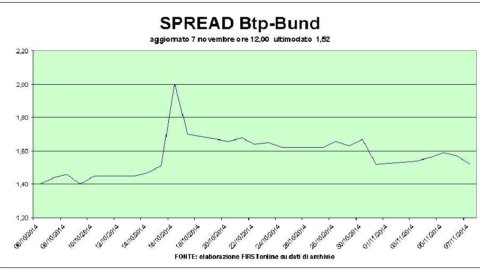我无法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我只是不记得我是如何结束的。 但也许它根本不重要,因为序言通常是无用的,只能用来争取时间。 真正有趣的是果汁,当你去除周围的一切时获得的珍贵蒸馏物,几滴如果你看到它们被收集在两只手之间会让你想起一旦你去除肿块并撇去和过滤之类的东西,简而言之,如果你去掉多余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多少了。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在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的脸上出现了那种愚蠢的表情,看起来机械、失控,你对自己说“这里,现在出事了”。 我已经被困在电子产品大卖场里好几天了,我什至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如果你想到那些在矿井中被关闭数月并可能在那里脱水、饥饿、冷冻而死的人,这个消息并不令人震惊,甚至与那些最终误入狭窄矿井的人相比也不那么令人震惊当他们沿着乡间小路静静地行走时,又长又黑 崩溃!,他们脚下的一块腐烂的木板断裂,使他们坠入深渊,离世界只有几米远,但离可以拯救他们的人足够远。 新闻的犯罪新闻与我无关。 现在我在这里有食物和饮料(有两台出售零食、饮料和咖啡的自动售货机),温度也不错(然后,所有的电器都在那里,你想要空调吗?)。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是,振作起来:昨天,被关在这里的绝望时刻抓住了我,我蹲在角落里抱怨,在裁谈会部门,我在见谁? 猫王。 我说他,猫王,国王,明白吗? 他自豪地留着香蕉卷发和浓密的鬓角(管他呢,但他毕竟是猫王),穿着经典的白色西装,亮片,亮片,流苏袖,踝靴,那种姿势,那种步态,他拥抱吉他就像一个女人,从头到脚都是他,南非祖鲁人会像婆罗洲人一样认出他。 他走近我,用我的语言和我说话,而且还把单词拼写得很好(他妈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说意大利语,别问我,但他确实是)。
“伙计,别哭,”他告诉我。
谁哭得最厉害,我面前就是猫王。
他轻轻地把手指放在琴弦上,开始给我唱歌 是 完全 寂寞 今晚 他的声音,根据专家的排名,上帝保佑它可能不是听过的最美的声音,但对我来说,它似乎总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某种无法解释的,近乎天国般的东西,如果你听到你会一直盯着那里一动不动地听,因为在那一刻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你感兴趣的了。
我随着歌摇头晃脑,像个傻子,闭着眼睛笑得像恋爱中的少年(只缺了身边的小心脏,像爆米花一样升起噼啪作响),我似乎也听到在后台纠正。 我想象着浪漫的散步、交叉的双手和亲吻:亲吻脸颊(啪!); 成型的吻(schiok!); 舌吻(嘶嘶声!); 无舌的亲吻(呃!); 难忘的吻(哇!); 亲吻忘记(重置!); 偷来的吻(ne-ni ne-ni ne-ni!); 追吻(嘘!); 要求亲吻(亲吻?); 亲吻从未有过(操!); 失去亲吻(不!); 找到亲吻(哦耶!); 持续几秒钟的亲吻(再见!); 永无止境的亲吻(请勿打扰,请……)。
亲吻结束。 然后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男孩,男人,成人,所有的亲热,我会做的,也许不是作为一个老人,但只要我能,是的,在这里,所有的亲热和那个歌曲作为配乐。 然后它结束了,我睁开眼睛,但猫王不见了。
“猫王! 猫王!! 猫王!!!” [作者注:逐渐增加感叹号以更加强调。]
我开始到处寻找他,但他已经消失了,消失了……我真的看到了他,那是一个异象,一个像宗教狂热者一样的幻影,那是什么? 我在大型商店转了一圈,回到我看到它的地方,然后甚至没有时间喋喋不休地提出一些假设(假设 1:我出现幻觉,我疯了;假设 2:猫王只出现在选民面前;假设 3:这是一个梦,这一切从未发生过;假设 4:也许天花板上的面板或电缆脱落了,它掉了下来, 繁荣!,它击中了我的头,所以现在我正在经历一种奇怪的生死经历; 假设 5:他们正在写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或者他们正在写一个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的人; 等等,关于太荒谬而不真实的故事的假设,例如适合梦幻般的,有远见的电影的平行维度和情节,可以这么说,就像大卫林奇一样)在CD部门我看到其他人,我说“其他人”,而是 Frank Sinatra 本人,哦,是的,我没记错,The Voice,Ol' Blue Eyes,Frankie,随便怎么称呼他,就是他 [作者注:我有意省略了昵称 Swoonatra,在意大利它从来没有听起来这么好]。 他看着我,对我眨眼,然后说“跟我来”(他的意大利语也很流利。好吧,但他是意大利血统,或者他一定是和猫王一起上过语言课程)。
我跟着他,你怎么能不跟着弗兰克辛纳屈,看到他走路我想请他重复魅力。 开始哼唱 如 飞 me 清唱,我已经欣喜若狂. 我们到了电动扶手椅部,他示意我坐下,沉默了一会儿。 我将靠背向后倾斜,直到我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感到舒服(这些扶手椅还不错,它们甚至具有振动效果!),同时他用脚敲打以发出节奏。 我看到麦克风神奇地出现在他的手中——但这很奇怪,我敢肯定他以前没有——音乐开始了,小号、钢琴、低音提琴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他及时打了个响指, 再次 如 飞 与 Me 但这一次就像在音乐会上演奏一样,这是一场只为我而设的现场表演,头还在动,到处摆动,我像个傻瓜一样闭着眼睛微笑,我飞过大型商店,超车他,再次向上,越来越快,今天是白天,我从云中出现, 噗!. 开始变冷了,天黑了,漆黑一片,从未见过的黑暗【心理医生注:作者强烈要求的矛盾修辞法!】,我在太空,无边无际的太空,行星,星星,流浪卫星,航天飞机,太阳、月亮、地球——我看到一只猴子敲打着那边的一堆骨头,发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施特劳斯 – 耀眼的灯光,紫-黄-绿-红-蓝色谱,一个星体胎儿,然后出现的黑色巨石,向我走来,接近,即将压垮我,但不,我是巨石,是我,我把他们都碾碎了(但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那么大而威风又有什么用呢?)。 然后我想了想,又开始下降,我不再是巨石,我移开,我像一个碎片,一团火球一样坠落,我从黑暗中出来,我从寒冷中出来,我刺穿云再一次 噗!,又是一天,到了大型商店,它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回到里面,微笑,闭上眼睛,我像个傻瓜,头在动,左右摇摆,睁开眼睛:音乐消失了,弗兰克辛纳屈走了!
“坦率! 坦率!! 坦率!!!” [作者注:我重复感叹号的概念,然后我必须使我的文体选择具有连续性。]
他也抛弃了我,我想知道为什么好事总是太少[作者注:创意危机时刻,我扮演小丑],但后来我听到喃喃自语,那里有其他人,在DVD部门,他们在这里是的,走近一看,我看得很清楚,他们有四个:奥森威尔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和斯坦利库布里克正在争论不休。 我开始朝他走去,但马上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人拉着我的胳膊,我转身,我看到了他, 我的天啊! (私信前传教士:不,对不起,我不是信徒,但这个表情给了我一个好主意],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Humphrey Bogart!Bogie 穿得像在 卡萨布兰卡,穿着他的雨衣和带乐队的帽子,然后他的手指间抽着香烟。 但为什么我看到它是黑白的? 我不知道,但这些色调很适合他; 事实上,这是我唯一一次认为电影中的色彩是多余的!
“你想做什么,孩子?” 他问我,微微挑起眉毛(如果你想知道他是否也说意大利语,是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声音多好!)。
“我想做什么? 那里,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 现在我去找他们聊天,在我看来这是最起码的事情。”
“他们跑不掉的,你知道吗?” 他笑着反驳道。
“不好了? 猫王和弗兰克辛纳屈呢? 他们在那里,片刻之后就消失了。”
“醒醒,孩子,”鲍嘉对我说,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注意到他的香烟从不熄灭。 他继续抽烟,而且始终如一。 但这到底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电影的把戏,然后我回头看了看。 “你的意思是在我睡着的意义上醒来? 总之,我很快就会在床上醒来,一切都会变成一场微不足道的梦?”
“嘿,孩子,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你从未见过 的向导 Oz“?
“你说得对,不能那样。 这太明显了,对吧?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在这里见任何你想见的人。”
我看着他,比以前更困惑了。 所以他继续。
“比如说,看看那边的图书区。 看到了吗?
一个男人出现了,一头黑发,一侧的制服刚好长到耳朵下方,留着胡须,显得很重要。 他身穿深色西装,在白衬衫外面打领带。 他急切地翻阅着书籍。
“那是谁?” 我问。
“Edgar Allan Poe,你想要它是谁?”他澄清道,甚至有点生气。
我又开始往前走,但转向架又拉着我的胳膊。
“也许你听不太清楚,孩子。 别管 Poe,他今天也很阴暗。 我认为他比平时喝得更多。”
“但也许不会有任何其他机会,”我抱怨道。
“但是,还会有更多。 我再说一遍:你可以在任何时间见任何你想见的人。 如果你想见柯南道尔,你可以去见他。 如果你想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你也可以看他们。”
“同意。”
我终于辞职了。
“一个问题,孩子:今年是哪一年?”
«好吧,当我来到这里时是 2011 年,但现在我不知道了。 嗯,可能是 2012 年,比如 2015 年,或任何其他年份。”
“从我那个时代开始,你就一直在编造东西,是吗?” 他对我说,环顾四周。
“已经。”
«告诉我,孩子,你是否也发明了一种机器来计算一个人一生中扔掉的所有钱? 我的意思是,那些人已经浪费了,那些人白费了。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东西将来可能会有用。”
“不,我们没有发明这个”我回答说,我回想起我浪费的所有钱和这种装置的天才。
“可惜了……那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多了。”
“是的,”我再次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我仍然迷失方向,好像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的名字是什么? 我该死的名字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坦率地苦涩地回答。
“我可以叫你路易斯吗?”
“当然,你可以随便叫我。”
我想了一下。 其实路易斯我不介意。
“路易斯,也许今天我们开启了一段美好的友谊。”
我回想起这些话,我敢肯定我以前听过。 不过,我不记得何时何地。 我所知道的是,当我在那里思考时,一团迷雾出现了,越来越浓,升起要抓住汉弗莱鲍嘉,把他带走。 转向架消失在该死的雾中,他也离开了我。
“汉弗莱!!!!!!” 【作者注:重复三遍他的名字感觉不太好。 但是,我不保存问号的总数。]
但他提到其他场合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我会在这里腐烂很久?
夜幕降临,仿佛最黑暗、最压抑的沮丧与我同床(哪张床?顶多一张电动扶手椅),沮丧是疲惫笨重的身体,下面是无底深渊,上面是无底深渊。没有希望的黑色无边的天空。 我想并记住了。 回想起来,我还记得。 我记得,特别记得。 我记得我最喜欢这种店,我记得老板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他三小时不间断,我记得 巴西 by Terry Gilliam,我记得所有在街上遇见我一段时间后问我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瘦甚至比以前更瘦的人(但我的新陈代谢很快,哎呀,你还没有明白了吗?),我记得喝过的啤酒、和朋友一起喝的啤酒和单独喝的啤酒、淡啤酒、黑啤酒、红色顶部和底部发酵啤酒、啤酒花啤酒、小麦啤酒、大麦麦芽啤酒、双麦芽啤酒、琥珀啤酒、白啤酒、泡沫啤酒啤酒,无泡沫啤酒,我记得我不喜欢和讨厌的迪斯科舞厅(但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记得那个高中同学想和我一起睡觉而我没有,因为我迷上了我的另一个女人,然后她离开了我,甚至没有让我远远地看到她[审查员注:你可以猜出意思,没有必要使用“f”开头的那个词],我记得我在九十年代穿的不可思议的簇绒(当然,我总是看起来 比佛利山庄90210), 我记得垃圾摇滚浪潮,当似乎只有垃圾摇滚浪潮存在时,我记得 Amiga 500 e 明智的 足球,我记得在学校的叉子和失败(因为我总是在玩 明智的 足球),我记得我祖母过去常常在星期天做的肉丸 pommarola(多么香!,我现在似乎也闻到了),我记得 Commodore 64 和电子游戏,我记得 Subbuteo 和我叔叔的游戏他赢了还取笑我,我一直记得打火机冒出火焰的可乐广告[作者注:我知道错误,但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巨人会来让我付钱给他提到这个名字的版税],我记得长长的萨克斯独奏是八十年代轻摇滚作品中的器乐插曲,我记得后座的汽车旅行和 Pooh-Dalla-Venditti 作为配乐(我发现自己听了多少次在怀旧的怀念中再次向他们致敬!),我记得短裤和及膝袜,蓝色牛眼鞋和我总是扔在草地上的小夹克,还有消失的金色卷发,我记得 ET 小时候去电影院然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不再记得我的名字或我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然后我又开始想了,我只想到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不该想的,去给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解释:死。 也许博加特的意思是我们都会在另一边相遇,然后会有很多机会再次见面:我死了,他死了,每个人都死了。 我又问自己,一万一千次:我会死吗? 我再想想。 我当然会死。 但是我会死在这个大商店里吗? 我会死而无所见 大-碗 由修拉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和 费利克斯 芬内翁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 Signac(这很好,我喜欢点画派运动!),我会在没有去过日本或澳大利亚的情况下死去,我会在没有学好英语的情况下死去(我说得好是因为它必须与我的课程中指示的实际知识水平相对应)并演奏一种乐器(但是,钹和三角不算在内),我会在没有完成阅读的情况下死去 寻找失去的时间 普鲁斯特的那本书在我的床头柜上放了很长时间,但这里没有副本! [作者注:其实在我的床头柜上有一本伍迪·艾伦的故事集,但我的角色更忙于阅读],但最重要的是,我会死而不会说出诸如傲慢、傲慢、顽固、银版照相、双色等字眼公开演讲或其他时候的术语,例如 never、testé、felon with acquaintances,只是为了展示我的万事通(我知道,这很丑陋,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而不是“诀窍”。我借此机会提出关于更换意大利语词汇中的两个术语的请愿书)! 然后我开始大声喊出这些词,就像它们是一个词一样,没有呼吸,然后出现了一种单曲(最美妙的是字母总数远远超过了 Mary Poppins 的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PROTERVOUBERTOSUCCIDUODAGHERROTYPICAL SINALLAGMATIC GIAMMAITESTÉFELLONE!!!
有事情发生。 我想如果我能一下子说出那样的话,而且从不喘口气,那么我就能做到这一切。 就在我还在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文字出现在我眼前,闪烁着大字:WHO CARES(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看过这个,但如果我看过,它会出现在平面屏幕上60 英寸,色彩鲜艳,图像分辨率高)。 谁在乎我是不是在这里腐烂,谁在乎我是不是死了,谁在乎我是不是看不见或做某事。 我在这里,我想见谁就见谁(哦,亨弗莱鲍嘉告诉我,我没有编造)。 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听到音乐的音量在慢慢增大。 我走近高保真系统和扩音部门,看到他们搭建了一个舞台,乐队在上面表演……还有……。 哦,我的-D哟! (我向前传道员重申,我对这个表达方式的使用不当),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摇滚超级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弹吉他,杰科·帕斯托瑞斯(Jaco Pastorius)弹贝斯(如果你不认识他,马上去看看他能做什么!),鼓手 Keith Moon 和主唱 Freddy Mercury(键盘位置仍然空缺,因为我喜欢的键盘手都还活着!)。 弗雷迪(他的穿着就像在 1986 年温布利音乐会上一样:白色红条纹西装、白色汗衫和黄色夹克)看着我,用手指示意我坐在前排(反正只有前排)。 当我坐下时,他走向麦克风。
«本篇 is 您, 家伙» Freddy Mercury 说(我指出他不会说意大利语,不像其他人。非传统万岁!),然后继续说:«在大型商店 奥德赛“。
一首新歌,特别为我写的。 这是他的声音,他开始动起来(呃,Freddy 动起来的样子!),Jimi Hendrix 和 Jaco Pastorius 用他们的乐器做着疯狂的事情,Keith Moon 开始动起来。 我陶醉了,陶醉了,着迷了[作者注:用来强化概念的同义词],这首歌也很美; 它持续几分钟,然后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和几个小时,整个晚上,总是一样,以至于我睡着了,早上醒来。
我们回到原点。 超群不见了,但我还在。 我无法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或将如何结束的。 另一方面,你对一个连名字都不能告诉你的人有什么期望? 也许像这样的商店不应该一直营业,或者至少休息一天? 有没有可能我的饮料和食物供应永远不会用完? 但总而言之,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您是否必须找到解释或不在乎并充分享受它? 我决定不再问自己任何事,我会这样生活,想见谁就见谁,想见多久就多久。 理性的解释该死,如果有的话。 抱怨也见鬼去吧。 我是认真的,我改变了我的人生哲学(低声说:实际上是汉弗莱·鲍嘉说服我说这些话的。他在这里,他就在我旁边,黑白两色,中间不停地吸着香烟他的手指。我发誓,他没有用枪指着我!)。 这就是整个故事。 我现在要走了,几分钟后我在图书区与奥斯卡·王尔德有个约会。 我们会一起喝自动售货机里的茶,同时他会用他的格言逗我开心。 唯一的问题是他让我穿得好,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这里只有乐队 T 恤,我穿的衣服不太适合和他这样的花花公子见面. 不过这个问题不关你的事,我会自己处理的。
“我们走吧,路易斯。”
“是的,汉弗莱。 嗯,你看,既然埃尔维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能不能借我一件雨衣和帽子,有没有机会?”
“甚至没有死,路易斯。 连死都没有。”
香烟继续抽着。 烟雾与雾混合。 博加特和我消失在里面。
Mirko Tondi 出生于 1977 年,他在 Troisi 奖(2005 年)中获得特别提名,在选集中发表了诗歌和故事(包括蒙达多利犯罪小说的故事,2010 年),一些他喜欢将其定义为“实验性”的小说知道是否真的如此。 他负责佛罗伦萨(他还在那里组织文学俱乐部)和维亚雷焦的写作研讨会。 他的最新出版物由 Robin 出版,是 看见双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