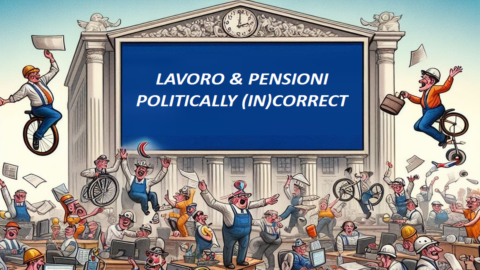解释主权债务危机的起源 比利时经济学家 Paul De Grauwe 比较了西班牙和英国的情况. 危机爆发时,英国公共债务比西班牙高出 17 个百分点,但市场瞄准了这个伊比利亚国家的债务。
而这种行为的原因在于,根据 De Grauwe 的说法,欧元区国家以“外国”货币发行债务,投资者不确定债务国是否有必要的流动性来偿还到期的债券。 因此,危机的根源已经存在制度性因素: 货币联盟诞生于欧洲,没有政治统一和欧洲中央银行,在没有欧洲力量支持的情况下, 干预能力有限 要采取行动,必须获得成员国的同意,尤其是强国的同意。
这一体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 Ecofin 理事会、欧元集团或欧洲理事会在连续几波中做出的决定仍然没有效果。 例如,考虑在 首脑会议 布鲁塞尔 28 月 29-XNUMX 日 直接为西班牙银行提供高达 100 亿欧元的资金,并鼓励购买困难国家的政府债券 - 避免利差过度扩大 - 通过临时救助机制,以及何时生效,由欧洲稳定机制。 重要的决定,但仍然是一纸空文。 面对利差的进一步扩大和金融市场的崩溃,据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在一份后来被巴黎否认但得到帕塞拉部长含蓄确认的联合声明中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决定,而没有考虑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不信任欧洲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不受赋予自主权并因此能够采取行动的政府的支持。 参考点仍然是各国政府和单个国家而非整个地区经济的宏观经济图景. 如果不在制度层面上决定性地改变步伐以形成一个受欧洲议会民主控制的欧洲经济政府,货币联盟崩溃的风险似乎每天都越来越难以控制和最终避免。
实际上,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应仅限于通过区内各国的限制性措施促进公共财政的整合。 尤其, 在等待批准的情况下 税收协定 欧元区成员国必须使预算基本平衡,将平衡规则写入宪法 (或在类似级别的立法行为中:这就是法国人会做的),以便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向欧盟法院提出上诉,并缩小差异当前的债务/GDP 比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定的 60% 水平之间的差距。 除了由于未能考虑必须将余额强加于预算的当前部分而债务必须用于为投资融资的黄金法则而可以提出的意见之外,必须就预算的内容提出两个意见这 税收协定. 首先,没有发展就没有财政整顿。 这是公共财政的“经验法则”,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赤字增加半个百分点。 但如果各国不能再实施基于债务的扩张性政策,则必须将这一任务交给欧盟。 欧元区既没有负责增长政策的政府,也没有由其自身资源提供资金的预算,无法促进必要的投资,使欧洲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观察与民主有关。 在欧洲危机中,公民生活的基本决定越来越多地由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机构做出。 正确的是,默克尔总理要求,如果使用从德国公民那里获取的财政资源,则有一个政治联盟能够控制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 但德国政府随后并未主动启动必须通向政治联盟的进程。 Hic Rhodus, hic 盐. 问题是立即发起一项政治倡议来扭转这一趋势,这种趋势助长了非常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并使公民越来越疏远欧洲统一进程。
在 2012 月底的欧洲理事会上,各国政府自行设定了反思阶段结束的最后期限(XNUMX 年 XNUMX 月), 通过将所有权归于自己来歪曲条约的文字和实质内容 (所有权 英文)的条约改革,并将政治联盟仅限于经济和货币联盟。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满足充分意识到无国籍货币内在弱点的市场,它不能保证公民的民主合法性,因此不能保证决策的可接受性,也不能确保欧元区的有效性和效率。 Tommaso Padoa Schioppa 说,有必要克服单一“欧洲经济选区”与 XNUMX 个但很快将有 XNUMX 个“国家政治选区”之间的精神分裂症。
欧盟迫切需要一个宪法层面,在我们所有的民主国家宪法都是由制宪议会选举产生的. 几个星期以来,Il Sole 24 Ore 一直在竞选欧洲合众国,将其作为拯救欧元的唯一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危机的恶化要求通过制定项目条款、方法和执行议程来继续开展这项运动。 罗马条约的起草、批准和批准历时两年半。 通过欧洲中断行为,我们可以在 2014 年底之前从欧盟转移到欧洲合众国(这与意大利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时间相吻合)。
Pier Virgilio Dastoli 是意大利欧洲运动 (CIME) 的主席和欧洲议会 Spinelli 小组的协调员,曾担任 Altiero Spinelli 的议会助理。
Alberto Majocchi 是帕维亚大学金融学教授。 他是经济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ISAE) 的主席,曾任欧洲联邦主义运动 (MFE) 的政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