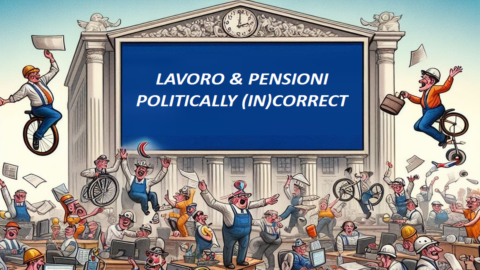想法很重要。 从何时起 启蒙运动使我们意识到哲学的影响 在计划行动中,影响行为的是观念,它们的辩证对立和利益的多元化:革命世纪(英国、美国、法国)是由现代人的政治思想产生的; 马克思启发了工团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尼采虚无主义与艺术; 史密斯、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
作为实干家,我们必须以每个人的力量为发展社会共同思想的论证做出贡献。 感谢 Franco Gallo 教授, 在最近的文章中 “未来不是死胡同”, 由 Sellerio 出版,反映了他作为税务学者在一般政策原则方面的专业经验,具有强烈的文化敏感性。 我们最近在 Luiss-Guido Carli 与 P. Baratta、A. Laterza、F. Locatelli、B. Tabacci、T. Treu、G. Visentini 和该书的作者一起介绍了这本书。
Gallo 认为全球化会压缩公民的社会权利: 正是论文为反思提供了系统. 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规则占主导地位,如果不是消除的话,也会减少国家法律在塑造社会权利方面的主权。 欧洲没有捍卫自己的市场至上地位,从而导致社会权利成为次要目标。 在这种市场支配的背景下,加强对财产权的传统解释,而不是宪法保护,可以解释为 它应该被理解为社会价值的功能性权利.
它遵循的是对财产支付能力的宪法原则范围的验证,对此宪法法院的判例并未承认教条的绝对价值。 最后,讨论了社会权利与最近在实施社区计划中加强的国家预算平衡之间的困难平衡。 因此,欧盟法律体系对社会价值的不敏感就凸显出来,除了条约中提出的原则确认之外, 仍受市场制约: 预算余额。
我注意到在这次讨论中我 社会权利被理解为国家配置的福利 管理,按照新政开始的方式; 在大西洋国家,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矩阵哲学得到巩固(Muller-Armanck 和 Ludwig Erhald)。 但这并不是组织个人幸福的唯一技术。
与其说经济在全球化中的进步使新政的经验陷入危机,不如说它们在昂贵的官僚机构中的结晶,无法适应事物的演变: 我们记得加利福尼亚州对肥大税务员的反抗; 我们还回顾了已经不合时宜的对航空运输的过度管制,以及由于价格急剧下降而解除管制(重新管制)的成功。 根据哈耶克、蒙特佩莱格里诺社会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尔和里根的最小国家政策得到了推广(“政府是问题所在”), 由英国工党自己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
国家不一定要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以满足个人的幸福权; 它也对市场经济的组织感到满意,而且更好。 市场技术即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是足够的; 各种权宜之计纠正了不可避免的财富不平等,例如负税, 公民收入,让父母自由选择教育路径或个人选择他们的健康保险的资金支出。
然而,两个主要的误解使市场实践偏离了其哲学的理论意图。 我们理解那些今天将社会权利的牺牲归咎于市场,甚至更早的人的批评。 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为了压缩工资。 市场被理解为自然界的一种情况,而不是国家法律的产物,被扩展到国际或全球范围:它发生在美国,伦敦,但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在在全球背景下,这一想法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并影响了其经济,尽管在最受保护的欧洲部门中强度不同。
所谓的放松管制已经蔓延到影响市场当局干预的程度,市场当局选择对其使命进行明确的限制性解释,允许更严格的限制(例如货币基金)的难以捉摸的现象。 相反,市场是法则的创造. 为了增加收入,企业愿意搪塞,并倾向于垄断作为其自然条件; 垄断通过权力的勾结改变了市场,这些权力较少受到竞争的限制,获得了溢出到政治领域的力量。 仅仅保证企业和消费的自由、所有权和透明度是不够的。
市场必须规范 拥有完善的私法和充分的司法保护; 它必须在公法的授权下对公司施加; 必须根据部门对其进行加权:工作和社会关系发现承包商之间的不平衡如此严重,以至于证明逐步干预集体谈判是合理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第二个误解,金融也被理解为一种能够让市场自然自由的活动。 如果它没有产生货币的潜力,情况就会如此,只有在激进的概念中,货币才会被委托给私人交易,脱离国家的政治主权。
金融,银行,用信用创造、传递、传播购买力,也就是货币。 随着约束和壁垒的压制,包括国际(资本流动),迫使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投资,金融从实体经济中的交换工具也变成了,最重要的是,投机工具: 转移财富,而不是创造新财富. 调查过这些事件的学者解释了 2008 年最近的危机,主要是在放松金融管制后美国法律体系发生的创新:
– 全能银行,现在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而不是存款融资;
– 集成产品;
– 他们的证券化;
– 衍生品。
该系统产生了一个无用且代价高昂的私人金融官僚机构; 市场退化为寡头政治。 我们回顾: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以及它们堕落为暴政、寡头制、民主制(民粹主义)。 对于经济学家 全球金融膨胀造成了不平等 在我们国家,通过压缩工资和需求; 作为社会历史学家,他传播了中产阶级的叛乱和民主国家的选举运动(A. Tooze)。
该怎么办? 混合(社会)经济的危机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在没有适当规则的情况下取代市场已经开始了整合和集中的过程,这能够减少竞争,阻碍市场本身,也就是竞争。 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对竞争的更严格监管的不一致现象解释了拟议的修改,这揭示了对世界经济组织寡头垄断方向的承认。 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规则,首先是在国际层面,以逃避美国政府的民族主义诱惑(连WTO都处于脑死亡状态)。
但正如现在方向相反的候选人特朗普所说,需要彻底重新考虑金融的作用。 美国金融引发了危机,但最终取得了胜利。 不仅美联储掌握了危机 作为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最后贷款人; 美国全能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胜利可能转瞬即逝:据权威评论员称,危机的原因仍然存在。 更一般地说,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政治思想的倡导者不仅谴责时事,而且谴责所谓的财富形成和分配扭曲的恶化。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激进的市场哲学逐渐出现了适当的力量,不把不平等视为贬值; 他们或许不会遗憾地看到全球化中寡头之间的谅解,尽管是不同类型的。 如果我们读斯蒂格利茨 (人、权力和利润) 我们看到共和党政府在美国的这种堕落(对我来说是痛苦的)。
欧洲是作为一个经济条约而诞生的; 在货币和金融联盟中,它正在达到联邦水平; 走向政治联盟。 但追求条约第一条规定的价值观,在其他部分,在人权公约中,是各国的责任,是的,在欧洲理事会的控制下,但无权替代干预措施:它可以制裁,直至“排除”。 社会权利委托给各州,也得到共同体的财政支持; 即使这会随着共同预算的可能延长而扩大。 和 Gallo 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对联盟发展的限制,因为过度整合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脱欧意识强的国家中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盖洛所关心的意大利,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Ugo La Malfa 提醒我们,欧洲的替代方案是地中海沿岸非洲国家的专制; 我们的条件不允许我们考虑英国脱欧。 意大利必须在欧洲管理。 然而,就人口和经济而言,我们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远不及意大利。 F. Gallo 的答案是在我们的维度上做得更好,因为有太多的主权可用; 与其将自己封闭在企业保守主义中,每个机构都捍卫自己的地位, 导致国家管理上的浪费:即使是紧缩政策也成为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不要浪费我们无法分配给投资成本的资源。
让我们回到思想的力量。 欢迎反省 个人 我们正在执行. 另一方面,我们的智力处理能力差 集体 我们周围的事件。 研究需要花钱,而且分配给它的资源很少:在大学、基金会、政治和社会代表研究机构,以及人们想要推进的报刊和新闻业。 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强调国家政治管理的偶然性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