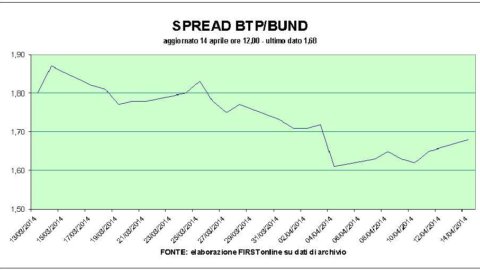阿兰诺的药剂师很想成为一名农民,当他们在星期天最好地参加弥撒时,他们会把罗勒叶放在耳朵和太阳穴之间的空洞里,就像木匠用铅笔做的那样。 他希望自己的手因为在乡下干活而干瘪、干裂; 回家后,吃完意大利面和番茄酱鹰嘴豆,在厨房的桌子上推他的妻子,没有任何仪式,仓促而兴致勃勃,就像你喝了一杯好咖啡但急着走。 然后,用前一天晚上吃的辣椒发出响亮的酸味打嗝后,慢慢靠近窗户,嘴里叼着牙签,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外面正在生长的玉米。
相反,除了懒散和略微懒散的步态外,他没有任何农民的特征。 他不高也不瘦。 他戴着眼镜。 他的头发很少,还有一点 pappagorgia。 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登记处的文员。 不是那些在柜台工作的人,那些你永远看不到的人,因为他们在内部房间,在档案室工作。 那些因缺乏阳光而拥有果冻般白皙的皮肤,以及因缺乏女性而出现潮湿、青灰色的黑眼圈的人。
根据药剂师的说法,农民是经过数千年与大自然的接触而选出的纯种。 他们从中汲取了智慧、手势和语言。 他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认为这次错失的机会是一种持续的、无法安慰的怀旧之情。
药房里,一位农夫走进来,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沉稳气息,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给肺充氧,仿佛置身于高山之中。 它活了过来。 血液再次在他的血管中流动。 他立即开始抱怨下雨妨碍了播种。 他诅咒冰雹,好像它伤害了他。 到了收获季节,他就添加到葡萄汁中的亚硫酸氢盐的剂量提出了建议,并建议在倾析时尊重月亮。 农民们不再听他的话,而是向他道谢。 不是感谢那些无用的建议,而是感谢那个脆弱的、没有经验的、奢侈的60岁男孩给予他们的坦诚和孩子气的友谊,给予他们过度但始终恭敬、幼稚、真诚的关怀。
那个年轻的面包师是那天下午的第一位顾客。 它又小又圆。 他总是带着新鲜出炉的面包的温暖气味。 她说话很快,发出音乐般的咯咯笑声,这为她赢得了 Cinciallegra 的绰号。 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一个。
为了忍受烤箱的高温,即使在冬天他也穿得像盛夏一样。 在药房里,她身体前倾,手肘撑在柜台上,衬衫里的东西全都露出来了。 在其他时候,那个幻象会让药剂师的一天快乐,并为漫长而疲惫的冥想提供起点。 现在,兴趣虽然还有点苏醒,但已经消失在千丝万缕的记忆中,不知道为什么,奶油炸弹浮现在脑海中:不是油炸的,而是在烤箱里煮的。 作为一名高中生,他为之疯狂。 因此,就在他思考糕点师的工作时,面包师告诉他,从阳台上点面包的格劳科叔叔告诉他,他已经用完了阿司匹林。 必须澄清的是,烟草商 Glauco 对每个人来说都早到了 Z我格劳克斯:他的绰号是因为博尔戈的孩子们在和他的两个真正的孙子玩耍时这样称呼他。 他发烧躺在床上。 药剂师乔瓦尼是他的侄子,他知道他也曾打电话来聊天、讲故事、编故事,就像五十年前他每周六晚上从罗马回来时所做的那样。
关上药房,我们的英雄因寒冷而双手插在口袋里,出发去他叔叔家。 向下走一百多米就够了,然后你就到了博尔戈:一个小广场,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家长式房屋,主要是附近有土地的农民居住。 药剂师出生在其中一所房子里。 九岁时,他与母亲和弟弟翁贝托搬到了村子上部,也就是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年。 在那栋大房子里只剩下他的叔叔:格劳科叔叔。
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穿过博尔戈广场,因为除了他的叔叔,他还去看望了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他最亲密的儿时朋友之一,他因病被关在家里一年多了。
圣诞节快到了。 灯已经亮了几个小时。 他们应该表现出一种他没有感觉到的欢呼。 曾经那些灯带给他欢乐和忧郁,现在他觉得它们充满敌意,好像它们对他来说也有麻烦,在那些节日的灯泡下,他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
他的为人哲学很简单:世人对美丽的人微笑,对丑陋的人做鬼脸,为了不屈服,培养同情心。 当你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心情愉快; 他们总是很开朗,随时准备大笑。 丑人懂得讲笑话; 美丽的人不需要,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这样做。
他既不属于美人也不属于丑人,因为他微不足道。 为了活下去,他在脑海中建立了一个平行世界。 在这个不同的维度中,他经常爱上他的客户。 他宁愿他们结婚,忧郁和痛苦,因为他喜欢相信他们的丈夫忽视了他们,甚至打了他们,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欣赏她们柔软的皮肤、她们的声音和她们的脖子。 是的,脖子,对于药剂师来说是一个毁灭的地方,一个女人所有的女性气质都集中在这里。 晚上睡觉前,他会回顾一下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想象她们收拾、打扫、熨烫、缝补,晚饭后,带着死人走向绞刑架的表情,上床睡觉。与她的丈夫。 他就这样度过了他的日子。 他的生命就这样过去了。
他走下塔尔西西奥 (Tarcisio) 的斜坡,与正在阳台上给天竺葵浇水的图里奥 (Tullio) 的妻子道别后,转过拐角。
***
他到达了格劳科叔叔的家,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那里保存着他的童年生活:他父亲还在世时在博尔戈度过的那段时光; 当羞怯还没有抓住他的时候,当他仍然能够奔跑以释放他的生活乐趣时。
在那所房子里,没有人从门进来。 有一扇常开的侧门,从侧门沿几米外的小路进入后院,从这里从厨房的门进屋,厨房的门从来不上锁。 院子四周围着一堵矮墙,矮墙和房子的墙围成了一个长方形。 在矮墙之外,绿色的冷杉树包围了那个空间,将它与世隔绝。 那里曾经是他一家人的暑假生活的地方。
现在只有 Glauco 叔叔住在那里,他是这座房子及其记忆的忠实守护者。 在通向庭院的车道的对面,从博尔戈广场看不到,因为它被房子隐藏了,低矮的墙壁被打断,可以进入被一圈树木围成一圈的小空地。 它们是金合欢。 其中有一些樱桃树。 这让你想到了婚礼的好处。 格劳科叔叔给他打电话 樱花园 为了纪念契诃夫。 当他谈到它时,他表示它是 诗人 从来没有如何 作家. 小时候,乔瓦尼 (Giovanni)、他的兄弟和他们来自博尔戈 (Borgo) 的一群朋友在那里组织了野餐,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主要总部来玩捉迷藏,并为他们的恶作剧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他们在那里庆祝生日、命名日和日历上所有发生在星期日和晴天的圣徒。
有时在晚上,在拜访了他的叔叔之后,乔瓦尼会在黑暗中进入樱桃园。 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开花植物的气味很浓,就像许多年前一样,浓得他仿佛能听到小时候和他一起玩过的朋友的哭声。 他追逐谣言。 在这其中他也认出了自己,这让他非常痛苦,就像死去的挚友一样。
乔瓦尼没有敲门,也没有开灯,就上楼去了他叔叔的房间。 他甚至可以闭着眼睛走路。 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就能辨认出那所房子的气味。 他深信,烹饪香料的各种气味,再加上住在那里的人的气味,构成了一种身份证:口气、须后水、牙膏、擦鞋的染色质和抽的香烟的牌子。 他确信,在那种独特的、可辨认的气味中,隐藏着住在那里的整个家庭的遗传遗产,不仅如此:还有它的历史、可怕的时刻和每个人生活中难得的幸福时刻。
走进他的老房子,他喜欢找到同样的气味。
格劳科叔叔正在读一本诗集。 他一意识到这次访问,就关闭了它,就好像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对话一样:
«每一首诗都有它的重心。 “孩子”是重心 星期六 村里的。 “享受吧,我的孩子,甜蜜的状态 ……”诗挂在这个词上,就像裙子挂在钉子上。 如果你把钉子拔掉,一切都会崩溃。” 然后,瞥了一眼椅子:«你赶时间吗? 你要去安东尼奥吗?»。
“是的,”侄子回答,在床上坐起来,隔着毯子捏住他叔叔的脚背。
“医生告诉我,他过不了年了。”
“他也告诉我了”,过了一会儿:“你好吗?”。 只有在他的叔叔和他的好朋友安东尼奥和帕斯夸里诺的陪伴下,他才能摆脱使他与众不同的害羞和尴尬的气氛。 他无法逃避的多样性。 就像一个不想要的、无情的口吃。
“只是有点发烧。”
“明天你会站起来。” 乔瓦尼开始慢慢起身,就像一个全身都是风湿病的老人。 他把阿司匹林盒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当他走到门口时,他补充说,“再见。”
格劳科叔叔把被子拉到下巴:“你知道,死于发烧或死于感染的丘疹是一种耻辱。”
乔瓦尼仍然站着,一只手扶着敞开的门扇,一言不发。 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格劳科叔叔开始创造寓言、故事和梦想的那些时刻之一。 但那一次他只是补充说:
“这种发烧不适合我。”
“不?”
“不。 我想死……在枪战中。” 他大笑起来。
“或者像莱斯利·霍华德在 石化林?!”
“对很好。”
“再见,”过了一会儿,乔瓦尼补充道。
“关于死亡,有一件事我无法接受。 我正在和安东尼奥谈论这件事。”
“什么?”
“这我说不准。 这么重要的事故,还不能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明天我过去。”
“向对方问好 Pitctor“
***
画家是安东尼奥的绰号。 他和妻子住在格劳科叔叔隔壁的房子里。 他与帕斯奎利诺同龄,被称为哲学家,是药剂师的密友。 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喜欢在格劳科叔叔家周围的白墙上撒尿。 安东尼奥是最棒的。 他能够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圈。 绰号由此而来。 他们到喷泉边喝水,把自己灌满。 半小时后,他们准备再次作画。
然后他们长大了。 当一个女孩经过 Piazza del Borgo 广场时,年轻人觉得有权发表评论。 并出现了诸如“风中的芦苇”之类的密码短语来拒绝太瘦的女孩,或者“跳舞的屁股”,“人人有牛奶”等。 相反,已经在他父亲的肉店工作的安东尼奥使用了属于不同语义类别的术语。 与此同时,对于一个女孩,他知道如何指出他可以从肋骨上获得的牛排的重量和数量。 在评估了腰部的硬度后,当需要表扬时,评论是,“在剪毛之前像羊一样走路。”
开门的是安东尼奥的妻子朵拉。 与药剂师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源于曾经是小玩伴。 他一言不发地陪着她进了卧室。 安东尼奥站在窗边。 他看着广场,额头贴在玻璃上。 乔瓦尼走近,也停下来看着博尔戈广场。 安东尼奥,没有转身:«你看到那些女人了吗? 即使在我死后,他们仍会继续去喷泉处注满水盆。 然后他们会把她放在头上,然后像 Vatusse 女王一样挺直,他们会回到温暖的家。 生活将是一样的,永远。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在这时,阿尔贝托过去了。 他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一个真正的农民,现在,在他的晚年,他靠做鞋匠凑了一些钱。 安东尼奥用一种惊奇的语气补充道:“然后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对每个人的怜悯。 即使是阿尔贝托那个混蛋。 自从他想把那只残废的山羊卖给我后,我们就一直没说话。 回忆? 但谁知道我是不是在骗他,因为我一无所获。 简而言之,现在我要拥抱那个混蛋。 永远带着烈士的面孔。 然而我爱他。 我为他的晚年感到遗憾,为他帮助妻子时默默而矜持的爱而感到遗憾。 他把她当女王一样养着,那个半女巫。 但我也会拥抱她。 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女巫!»。 然后,慢慢地,他回到床边的扶手椅上,叹了口气补充道:“为了让世界正常运转,我们都应该接近死亡。” 他拿起填字游戏,好像在读:“格劳科叔叔?”。
“他很好,”乔瓦尼回答,在他对面那张著名的脏兮兮的扶手椅上坐下,弹簧虽然坏了但非常舒服。 他盘起双腿,手指交叉在脖子后面。 然后他补充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的。 好一点。” 然后,叹了口气,将手肘撑在扶手上,将自己拉起来向前,低声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你会觉得很奇怪,也许很疯狂,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 .我快死了。 请原谅我对你说话粗鲁,但我不能大概,一切都必须清楚”。
乔瓦尼也向前倾了倾身。 安东尼奥为了不让多拉听到,在一千次尴尬的停顿之间继续压低声音:“死亡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困扰。 我等不及要摆脱它了。 是的,我很害怕,但我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如果其他人能做到,我也会……但这不是我想和你谈论的……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是关于朵拉的……你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过一段时间你就结婚了一切都成为一种习惯。 你的妻子不再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她……而是像对待仆人一样。 总之,我充满了自责。 你不结婚是对的……”
“我没有结婚,因为我做不到。”
“闭嘴,不如说你从来不想听我说话。 但是现在让我告诉你,在朵拉进来之前……那天晚上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 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 她是如此亲切,充满爱意。 但是你知道的……总之,去年五月,我已经生病了,我让她带了一束花: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在纸条上写了一句情话……没有署名……我觉得这样会更好玩,引起好奇心,然后告诉她真相……元帅夫人安娜收到的时候正在厨房. 他只对她倾诉。 总之,对于那个神秘的情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想到了。 我感觉到了一切。 安娜幻想着将市长和市政卫队列入可能的追求者名单,然后当他们将教区神父加入名单时,他们大笑起来。 在那些笑声中,我感到如此陌生。 我立刻明白,如果朵拉知道我送她花,就像送她菊花一样。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她这么开心了。 我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这是正常的。 很正常……我们没有孩子。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他有这个朋友。 以后你也试着多陪陪她,别丢下她一个人,像条狗一样。”
“所以? 你嫉妒?”
“不不不,你什么都不懂,该死! 我没嫉妒。 我快死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这样的废话了。” 他筋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
“我什至不能说话。”
“我不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告诉你,在我妻子的回答中,有一种微妙的、胆怯的奉承乐趣。”
“那你吃醋了!”
“不,我的朋友。 严肃点。 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请求这个帮助。 严肃点!”
“一个忙?!”
“是的,帮个忙,”他再次用手肘撑着身体前倾。 “我想把这种奉承留给你。 我至少希望这个是我的。 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 他倒回椅子上。 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要给朋友时间反省和理解:«你每个生日都要送她一束花。 下一次将在 28 月 XNUMX 日举行。 我绝对不会在那里。 你需要做 单 这。 现在我很抱歉,我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
他们保持沉默。 过了一会儿,乔瓦尼起身,带着在自己家里搬家的自然,慢慢走到窗边。 不是可以俯瞰带喷泉的广场的那一间,而是您可以从那里看到格劳科叔叔的房子的那一间,就在附近。 安东尼奥说:“你在想我们在那面墙上刷了多少遍吗?” 的确如此,乔瓦尼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她走到他身边。 安东尼奥闭着眼睛,气喘吁吁,就像刚刚跑完长跑一样。 他倒下了。 头微微偏向一侧。 乔瓦尼用手背摸了摸脸颊,说:“今天你没刮胡子”,然后说:“明天见”。 安东尼奥仍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你忘了吗?”乔瓦尼简单地回答道 没有离开了房间。
朵拉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剥土豆皮。 她还是那么美。 与他在高中时赢得跳远比赛时没有太大区别。 她个子不高,但很苗条,看起来很苗条。 鹅蛋脸依然保持着优雅,也许是因为那张白皙的脸上的小鼻子,和她那双绿色的眼睛一样明亮。 一条淡蓝色的手帕在脖子后面打结,用来收拢他的灰发。 他总是穿着吊带裤。 从远处看,他像个工人。 金属工。 但近距离观察时,很高兴看到那身阳刚的制服与她修长优雅的脖子和她节俭但总是坦率好客的微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那精致、庄重、沉着的举止有一种谦逊的气质,这也从他的声音中透漏出来。 背部总是挺直的,就像运动员一样,给她一种严肃的、几乎是严肃的感觉,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坐下来剥土豆。
她立马起身,像是被人发现做了什么禁忌之事。 他用桌上的厨房毛巾擦了擦手,没有说话,往门口走去。 乔瓦尼走出去,对多拉刚刚开始开着门看着地面的微笑报以微笑。 这是很少的话。 任何不认识她的人,都会以为她又聋又哑。
外面又湿又冷。 乔瓦尼转身看着安东尼奥家的门面。 他以为很快他们就会贴上他的死海报。 他想象着他们什么时候会放上自己的。 参加葬礼的人不会超过五六个人。 所有的痛苦和爱,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 在村子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绰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不透明的人,轮廓不精确,他是隐形的,不存在的。 有时他认为他已经死了。 当他走上图里奥的街道时,他反思了这一切,在他看来,生活似乎已经忘记了他。
格劳科叔叔每天至少去安东尼奥一次,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谈论他即将死去,就好像这是一部电影的情节。 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同意在葬礼结束后的同一天晚上,格劳科叔叔必须在窗边点上一支蜡烛。 安东尼奥会连续关掉它三次。 一句问候,是生活继续的标志。
他们在其他夜晚相遇。 在最后一次旅行中,乔瓦尼与格劳科叔叔和哲学家帕斯夸里诺一起去了。 这次没有尴尬的沉默。 安东尼奥很兴奋。 他总是说话。 他一一记起了格劳科叔叔的罗马故事。 他从乔瓦尼的弟弟翁贝托那里得到二手货。 他记得在博尔戈广场的喷泉周围诞生的初恋。 围绕它开始了他与妻子的故事。
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他拉着格劳科叔叔的胳膊对他说:“我推荐蜡烛!”。 他放声大笑。 他一出门,帕斯夸里诺就评论说:“来世是件好事吗?”
“有些人走在街上但已经死了”乔瓦尼回答道。
他们告别,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药剂师知道,一旦他回到自己的家,打开前门,他就会闻到那种旧衣服的味道,从衣柜里存放的衣服发霉。
***
春天来了。 安东尼奥于一月底被安葬在家庭礼拜堂。
睡前朵拉看着格劳科叔叔屋里点着的蜡烛。 在她看来,他似乎在窗后挥手致意。 但是时间过去了,想要摆脱丈夫生病的记忆的愿望开始渗透她的心,甚至在她的脑海里。
乔瓦尼信守诺言:他在朵拉生日那天送花给她。 而这,也多亏了春风,重新激活了朵拉生锈的想象力,但最重要的是它点燃了安娜的想象力,它开始发酵并提取最荒谬的假设,就像从魔术师的帽子里出来的一样。
一天晚上,乔瓦尼在拜访过格劳科叔叔之后,顺道拜访了朵拉,送来了一些药物。 她的脸因发烧而通红。 临走前,他站在门口给了她最后的忠告,心里想着自从他进来后,朵拉一句话也没说。 他建议她把自己盖得更好,因为温度已经下降了。 恰好,她还是没有说话,拿起一旁椅子上放着的一件毛衣,放到了他的面前。 它是羊毛制成的,浅哈瓦那色,可能因为不断洗涤而缩水了。 所以多拉,伴随着这些动作,带着滑稽的鬼脸表示努力,先把头伸进去,然后伸出双臂。 有几秒钟,毛衣一直紧绷,像甜甜圈一样卷起,卷在腋窝下和胸部上方,胸部以这种方式被勒死,突出了它的坚实和丰满的一致性。 然后他终于把盖住她的毛衣下摆拉到了臀部。
那个艺术体操的数字让朵拉的身体散发出浓浓的女人味,扑面而来,融化了他血管里焦急的喜悦。
药剂师很想吹口哨就出去了。 他很满意,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慢慢地,小心翼翼,生怕情绪变淡,他沿着斜坡往上走。 从博尔戈的房子里,像神奇的雾气一样,炒肉的香味飘荡在广场上空。
从那天起,乔瓦尼开始更加频繁地去朵拉家。 他一言不发地欢迎他,但带着友善和兄弟般的微笑。 他说话的那几次,就像是在伤口上抹了药膏。 他的话以歌曲的形式传到药剂师的耳朵里,带着催眠师的迷人温柔。 他现在觉得他罕见而简短的演讲充满了深刻的意义,隐藏着崇高的感情,这些感情由于谦虚或谁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崇高的原因而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 现在她的一切,哪怕是一个喷嚏,都散发着妖娆的风姿。 他通过讲述他的一些客户如何乱写药物名称来逗她。 甚至有人吞下了栓剂,认为它们是药片,在药房里他抱怨它们有多苦。
他一直很好地扮演女士朋友的角色。 他既没有阳刚之气也没有女人味的外表使他们安心,使他们免于任何形式的竞争。
他们还谈到了花束。 多拉尴尬地笑了笑,承认她担心这是某个危险的疯子的举动。 我们的药剂师对该报告感到满意。 他喜欢坐在那个厨房里,呼吸着屋子里的气味,看着壁炉两边的墙壁,上面挂着晾干的辣椒冠,就像来自古代文明的护身符。 他明白,即使没有必要,他的来访也是受欢迎的。 他并不介意将它们与自己进行比较,将其与一种无用药物的安慰剂效应进行比较。
一天傍晚,还是春天,药剂师从格劳科叔叔那里回来,遇到朵拉,朵拉提着一筐湿衣服挂在屋前。 然后他大胆地做了一个让他吃惊的自发手势:他摸了摸她的手,问:“你好吗?” 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一股焦躁,让他有些动摇。 她没有回答。 他的唇角微微翘起。 那是一个微笑。 然后他微微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我过得去=. 乔瓦尼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她说:“你明天来吗?” 我准备了酿辣椒»。 这次是他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不能说话。 他以为他听到了“你明天要来吗?” 同谋的气息,充满了影射。
他没有回屋,而是开进了格劳科叔叔的车道,径直走进了樱桃园。 刺槐的香气浓郁得让人头晕目眩。 空气很温暖。 一条绿树成荫的小路从花园开始,只有在家的人才能使用。 再往下,它连接到一条下行到“fossato”的小路:一条只在冬天活跃的溪流。 在夏天,它变成了小池塘,里面满是蝌蚪和唱歌的蟋蟀。
浓浓的黑暗为乔瓦尼的脑海提供了他喜欢记住的画面。 还没到路,走到一半,草木茂密了,有一段路,两旁的树枝在顶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拱顶状。 所以这就像穿过隧道。 他们称之为“洞穴”。 乔瓦尼在黑暗中再次看到了春天的景象:一簇簇白色和紫色的风信子花簇拥在通向大路的路口两侧。 再往下,报春花、仙客来和雏菊铺成的地毯增添了色彩。 进入那条大道,就如同进入了印象派画家的画中。 夏日闷热,洞中清凉。 前一年干枯的树叶在你的鞋底下发出沙沙声,震耳欲聋、催眠的嗡嗡声,再加上千只筑巢鸟儿的鸣叫声,使它成为一个迷人的地方,博尔戈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挥想象力这个世界的内幕故事。 当一个人想做一些越轨的事情时,就会去“洞穴”:越界就是爬树。 这是严格禁止的。 他们去把湿面包放在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要照顾。 就在那儿,不到五十年前,乔瓦尼突然在朵拉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就那样。 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考虑了很多年。
约翰的访问继续进行。 朵拉很高兴接待他们,但仅此而已。
冬天已经来了。 一天,元帅应邀与他的妻子安娜共进晚餐,晚上散步后去了多拉的家。 周围很少见到他。 又高又瘦,笔直如纺锤,还保留着老者不老的俊颜。 待人接物时,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执勤时的严肃、端庄的语气。 但他能够微笑着,偶尔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他的妻子安娜从下午早些时候就在那里。 会谈围绕为新教堂塔楼筹款展开。 账目没有加起来。 帕森作弊? 这是安娜最喜欢的话题,除其他外,她坚持认为送花的是他,教区牧师。 朵拉的脸上时而浮现出彬彬有礼又听天由命的微笑:她尊重教区牧师,安娜恨他,就像她的父亲,公证人一样,全城人又恨又怕他。
元帅进来时,挂在壁炉钩子上的大锅里的扁豆已经沸腾了一段时间。 朵拉踮起脚尖,正想从餐具柜最上面的架子上取下那袋盐,她只能用指尖去碰它,把它往里面推得越来越远。 元帅骑兵前去支援,伸到她身后,接过盐袋。 这种骚动在多拉脆弱、毫无防备的灵魂中造成了深刻的干扰:有那么一刻,元帅无意中碰到了多拉的下背部。 那只是一瞬间,但那天晚上多拉睡得很少,不确定元帅是无意犯罪还是有预谋。 而整个晚上,她都没有看他一眼,脸颊依旧红润,就像中学时代参加比赛时一样。
于是,在乔瓦尼来访的次数增加的同时,朵拉的心底也因为与元帅的插曲而生出一股焦躁的波涛。 他不得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一天早上,在面包师按惯例路过送面包的中间,朵拉给药剂师发了一张纸条: 我发现是谁派我来的到花。 今晚我等你. 乔瓦尼觉得自己被揭穿了,而且,将“我今晚等你”解读为爱的宣言。 焦虑袭击了他。 他应该如何表现? 他的爱情经历完全来自格劳科叔叔讲的电影。
他从衣橱里拿出那件夹克,衣橱里还有一点樟脑丸的味道。
他在春天把它收起来了。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在塔尔西西奥的街道上,沉浸在新的温暖中,他感到一种轻微的欣快感,一种对友谊的新意向,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新理解。 它闻起来像薰衣草。 他去找了理发师,理发师也给他剪了头发。 他想起了他的朋友安东尼奥。 他知道他得到了她的认可。 他自己曾建议他不要“像狗一样让她独自一人”:他的话。
一股令人安心的烤栗子香味从图里奥的房子里散发出来。
在敲朵拉的门时,乔瓦尼担心自己的耳朵会着火。 他试图拒绝假扮成客人而不是新郎的不愉快感觉。 朵拉把椅子推到一边,请他坐下。 在桌子上,她避免看他,把雪盘和常用的一瓶茴香酒放在桌子上。 一切都在没有丝毫声响的情况下发生,在两人最绝对的寂静中发生。 她身上没有穿五金工的工作服,只是头上包着一块手帕,看上去就像个农家姑娘。
突然多拉告诉他,是元帅送她花的。 她很确定。 乔瓦尼气喘吁吁,嘴里含着一半雪,一动不动。 朵拉继续说道。 乔瓦尼听懂了十分之一。 他听到:“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最好朋友的丈夫……我没有勇气看她……”然而,即使被从他脑中掠过的元音和辅音的隆隆声弄得眼花缭乱,他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什么正在发生他所害怕的事情,并因此将其隐藏在他大脑的最深处。 朵拉永远不会爱上他。 其他时候,他以不同的形式经历过同样的屈辱,同样的痛苦。 和其他时候一样,他想躲起来,想逃跑,以免让那个丑陋的故事传到他耳中。
在门口,关门之前,多拉求他回来看看她,因为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真诚忠诚的朋友的支持。 乔瓦尼独自站在广场中央,不知道该上去还是该下。 就在这时,鞋匠阿尔弗雷多的脸出现在他面前,他用双手握住他的双手迎接他,就好像他想亲吻它们一样,并把它们放在胸前对他说话,好像他想保留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她向他讲述了她与父亲的友谊,她为父亲生了一个如此聪明的好儿子而感到庆幸。 最后,她将她的 cipollino 气息吹到他的脸上,请他看看他生病的妻子。 还拉着他的手拖着他走。 乔瓦尼什么都不懂,他没有说话,他发现自己在卧室里,阿尔弗雷多的妻子躺在那里,她似乎已经死了。 以至于刚睁开眼睛,乔瓦尼猛地一惊,意识到前方是什么。 他后来回忆说,他建议咳嗽时喝煮酒,并立即吞下两片阿司匹林片。
阿尔弗雷多给他看了一张黄色的照片,照片的边缘有蛀虫在咬。 上面全是苍蝇留下的黑点:“现在我们老了,皮肤垂下来,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那是她的结婚照。 “你有看到? 我的妻子是一朵花。 我一直把她当作一朵花来对待,因为对我来说,医生,就好像这些年都没有过去一样。 我们有七个孩子。 一切都解决了,但很远。 我们一个人呆着。 不要紧。 我们爱彼此。” 过了一会儿:«所以这不严重吗?»。
“不会,你们还会在一起很多年。”
“有福了,生你的母亲。 祝福你。” 并亲吻了他的手。
他离开那所房子时更清楚多拉家里发生的事情。 他筋疲力尽,几乎无法行走。 但他已经重新进入了她的生活,虽然地狱般,但他更熟悉。
他走近喷泉。 从广场的中心可以看到厨房:每个家庭的心脏。 晚餐时间到了。 在亮着灯的窗户的窗帘外,不知名的影子在移动。 是家人。 碗碟声、椅子移动声、说话声、阵阵笑声:在那些房子里,生活在唱着它的歌。 乔瓦尼被禁止进入那个美妙的人类旋转木马。 他开始往上爬,慢慢地,弓着背,好像他肩上扛着他存在的所有重量。 他转头看向广场。 在那里,他小时候玩过医生、跳房子、捉迷藏和互相追逐。 对于博尔戈的孩子们来说,互相追逐是一种永恒的运动。 在那些日子里,博尔戈总是在庆祝,充满生机。 夏天,傍晚时分,当太阳停止燃烧时,随着孩子们的游戏,母鸡、鸭子和其他动物开始来来往往 从家里, 他们穿梭在马厩和房屋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就像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上心不在焉、犹豫不决的游客,在黄昏紫色的灯光下,淹没了鹅卵石铺成的广场。 天黑了,宛如仙境一般,一盏碳化物灯发出淡淡的光辉,从窗外透出,见证着简朴而温馨的生活。 博尔戈的心脏是它的正方形,在他小的时候,他觉得它更大、更广阔、更宏伟。 Borgo 的生活围绕着喷泉。 当他等待铜盆装满水的时候,镇上最平庸的消息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八卦,情人可以和他的爱人偷偷地和冷言冷语交流,而此时他在家里已经把盆里的水倒空了水。回到喷泉的借口。
我们的英雄叹了口气。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坐在一楼一扇紧闭的窗台上。 在图里奥的家里,有人在讲一个诙谐的故事。 在继续攀登之前,他再次回头看了看。 他的眼睛看到所有的玩伴,一个接一个,围着喷泉嬉戏。 “只要你想跑,幸福就属于你”,他想。
他想他又看到了一个布球,它在广场上翻滚,带着成群结队的孩子歇斯底里地尖叫,就像春天的燕子。
。 。 。
约翰布奇 (阿兰诺,1944 年)是一位街头摄影师,他将威利·罗尼斯 (Willy Ronis) 的名言变成了自己的话:“Je n'ai jamais poursuivi l'insolite, le jamais vu, l'extraordinaire, mais bien ce qu'il ya de plus typique dansnotre existence quotidienne, dans quelque lieu que je me trouve……Quêtesincère et passionnée des modestes beautés de la vie ordinaire”。 Bucci 是三本摄影书籍的作者,并为剧院撰稿。 在他的小说文本中 火车为 叶列茨 (2010)和 还买洋葱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