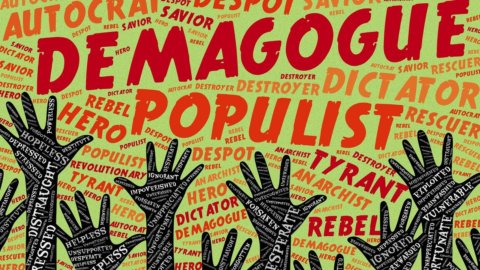从华盛顿到华沙,再到雅典和柏林,反建制政客继续以牺牲中左翼和中右翼人士为代价取得进展。 这似乎已成为新常态,4 年 2018 月 XNUMX 日的意大利选举只是“以一种相当引人注目的方式证实了一种普遍趋势”,即使最近的地区选举发出了不同的信号。
牛津大学欧洲政治学教授、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扬·泽隆卡 (Jan Zielonka) 是一篇论文的作者,他表示,今天的意大利代表着“教科书式的反革命案例”, 反革命。 自由欧洲的失败, 由 Laterza 在意大利出版,以一封长而清晰的信的形式写给他现已去世的导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他也追随他的导师的脚步,这位导师多年前曾使用相同的叙事语域写过一部作品。 Zielonka 分析了过去 XNUMX 年来自由民主国家发生的事情,并以非常批判的精神,通过承认该制度的失败来定义错误,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该制度,但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调整。
革命和反革命总是带来动荡,“我们还没有看到当前政治狂潮所产生的混乱和冲突的最坏表现”。 “新来者”对自由主义建制派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批评,但知道如何摧毁旧秩序并不意味着能够建立新秩序:“政府的宇宙不同于反对派的宇宙”。
所有增加国家支出和扩大就业者权利的巨大努力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反应,业务转移到海外,随之而来的是选民的失望,“新政府必须事先知道如何应对这些情况”。
媒体喜欢关注个人和政治背景,但应该“为这些有着全面变革议程的新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困境留出空间”。 将镜头聚焦于隐藏在政治口号背后的价值观和规范,将意大利视为欧洲正在开展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实验的特例”。 一个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实验。
一些人,甚至很多人,会乐于维持现状,甚至将时光倒流到“神话般的过去”。 许多自由主义者渴望回到“自由王国的美好时光”,不想看到任何改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经济利益比政治利益受到更多关注和保护,私人价值比公共价值更受珍视,现在“必须重新审视这些优先事项”。 对于 Zielonka 来说,议会改革不会产生奇迹,因此有必要在代表之外的其他支柱上建立或重建民主:「特别是参与、意见交流和辩论」。 自由主义不能再致力于“既不捍卫现状也不强加任何教条”。
民粹主义已成为几乎普遍的讨论话题。 事实证明,自由主义者“更善于指责他人,而不是反思自己”。 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解释民粹主义的诞生和缺陷,而不是阐明“自由主义垮台”的原因。 Jan Zielonka 的书正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不平衡上,它是“一直是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批评之书”。
今天整个欧洲都处于“混乱状态”,公民感到不安全和愤怒,“他们的领导人原来是无能和不诚实的”,他们的企业家显得愤怒,政治暴力正在上升。 Zielonka 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扭转历史的钟摆以及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的偏差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作者认为放弃“自由主义信仰”的一些中心点是不合理的:理性、自由、个性、权力受控和进步。 他宣称,他相信目前欧洲局势的困难可以转变为“另一个美妙的文艺复兴”,但这需要认真反思迄今为止出了什么问题。
在欧洲,政治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制度工程的艺术”,而不是“精英与选民之间的谈判艺术”。 越来越多的权力被授予非民选机构——中央银行、宪法法院、监管机构——。 “倾向于屈服于公众压力的政治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即使不是危险的。”
反革命政客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者,但“这个词具有误导性和污名化性”,而且根据 Zielonka 的说法,它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即废除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建立的秩序并取而代之产生它的精英。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绝不能养成“非黑即白的摩尼教思想”。
作为民主党人,绝不能讽刺选举选择。
作为公益活动家,我们不应该抱有人们突然“醒悟过来”、“又坐到我们身后”的幻想。
Zielonka 指出,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批评是错误的,而是要看看自由主义理想在社会和技术变革面前是否站得住脚。
对于自由主义者今天的困境,最常见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转向。 但是“自由主义是被贪婪的银行家绑架了还是它是自我放纵的理想滋生地?”
1989 年的革命围绕着民主、安全、欧洲、边界和文化等概念展开。 人们希望由不同类型的政治家统治,而作者担心“今天的情况是相似的”。 反革命政客不仅反对个别的自由主义政策,而且违背他们的整个逻辑,并“试图迎来新常态”。
一个国家能否负担得起更彻底的社会政策不仅是“统计事实的函数,也是政治选择的函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善和正义的看法。 相反,荒谬的是,那些建议为每个加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最低工资或奖金的人最终会“被新自由主义者贴上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然后 Zielonka 引用了 Andrew Calcutt 的话,他认为,与其责怪民粹主义,因为它“实现了我们已经启动的目标”,不如承认“我们在所有这一切中所扮演的可耻角色”。
只有通过深刻而明确的自我批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才能不屈服于反革命分子的前进。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通过适应现在变化的时代来回顾原则和教条。 这是 Jan Zielonka 唯一的出路,他在文中多次强调了他对自由主义纯粹和原始价值观的坚定信念。 那些不应该被抛弃的,而应该被重新发现的。 正是带着这种微弱的希望,他拒绝了读者 反革命。 这本书讲述了当前系统的退化以及那些想要与之抗争和改变它的人。 这本书是对改变、调整,最重要的是平衡的发自内心的请求。
里弗里门托图书馆
简·齐隆卡, 反革命。 自由欧洲的失败, Editori Laterza, 2018. 由 Michele Sampaolo 翻译原版 反革命。 撤退中的自由欧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Jan Zielonka 在牛津大学教授欧洲政策,并且是圣安东尼学院的 Ralf Dahrendorf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