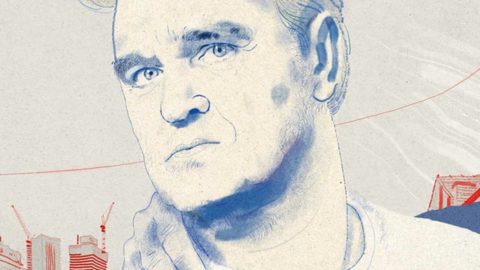幕布在黑暗的黑色舞台上升起。 有那么一会儿,远处传来一段几乎难以察觉的旋律,背景是忧郁的声音和低音调; 之后音乐停止,舞台开始亮起。 光线是白色的,很强,场景的中央是一张木桌,也是白色的。 上面坐着一个黑发女人,赤脚,穿着破烂的衣服,她的腿和脚悬在空中,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 他低着头,软弱无力,仿佛毫无生气。 她面前是翻倒的椅子,和桌子一样白。 光强度增加。 女人抬起头,直视前方,越过椅子和舞台,望向观众; 他的脸化得太浓了,没化。 光线再次增强,但仅限于舞台上。 女人瞪大了四周的眼睛,黑暗的房间里,取出一支笔,在手中翻来覆去,掂了掂。 一切都很安静。 最后他离开桌子,开始讲故事,手里拿着笔。
有时——有时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他。 空气中的一缕阳光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一个下雨的星期天,几个小时的孤独和无聊,突然间我变成了莫里西,说真的,我成了史密斯乐队的前主唱,我生命的终结和我的痴迷,我的谴责。 我可以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连续几个小时蠕动,拖着自己的声音和身体,将自己献给整个世界、观众和我空荡荡的房间。 我想我可以再做一次,即使在这里,爬到桌子上,用这支笔作为麦克风,作为权杖。 但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你不关心我的声音:你想知道我的伤口、我的痴迷、我的疾病等等,甚至我的幻想和我的暴力,我想,就像如果我和莫里西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他与我和我的“病”无关,如果我们想那样定义的话。
因为对你来说,我心爱的 Moz 只不过是另一位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星,是弗兰克辛纳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约翰列侬和谁知道还有谁的混合体,没有什么独特或超然的; 从音乐上来说,你看起来不太聪明。 当我问你是否认识他时,我知道你会说不,或者至少你会依偎在一起,也许假装你听过一两首歌,以获得我的好感。 但是当我严肃地反驳说:“莫里西可以救你的命”时,你不应该笑那些笑容,我的审判官,你也不应该在以后的访问中光顾我,否则你会直接进洞而不是我的好恩典。我的仇恨,在我的受害者中。
我不能确定,但我想我第一次见到 Morrissey 是在 1995 年,那是我 XNUMX 岁生日的冬天和 左撇子语法,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女孩,但我已经开始在孤独和屈辱的青春期与煽动性的梦想和 不正当的, 斜体是强制性的,这是在图书馆或床上度过几天的沉思的结果。 不用说,Morrissey 在 XNUMX 年代在曼彻斯特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我出生在曼彻斯特,在中央图书馆的犯罪部门”——在诗歌与孤独、痴迷与雨水之间,这是我们关系的基石之一. 另一个支点是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声音和他的话语,他在舞台上和生活中的姿势; 谈论简单的歌曲将是简化的、不公平的。
事实上,突然间,就好像有人,一个既可爱又该死又温柔叛逆的人,溜进了我的房间, 唱出我的寂寞,我的辉煌和我人类的苦难,我无法爱,也无法被爱。 Morrissey 没有向我承诺性、吸烟、毒品、火星生活或其他便利设施,但他知道如何唱歌和和我一起受苦,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他凄美而暧昧的诗句向我揭示了我们在一个绝望的世界中孤独,这很好; 或者它就过去了,这就足够了。 我十三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我进入了成年和第三个千年,我知道“2000 年不会改变这里的任何人, 因为每一个传说中的承诺飞得如此之快”,但他教会我欣赏我口袋里和生活中的空虚、我的孤独和无聊、我的蔑视、我的喜怒无常、我在厕所里的血迹。 简而言之:莫里西帮助我活了下来,他给了我一个身份和一个值得爱的人,他。 他出来的时候 爱尔兰血, 英国之心 (“地球上没有人让我害怕...”)当时我二十四岁,我决定离开意大利,去曼彻斯特的竞技场看他的现场表演,那是一场表演 难忘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人群把我挤在障碍物和肘部之间,向他伸出双臂,在舞台上,穿着他的白衬衫,笔直而巨大,不真实但真实,高大,有目的,发光,有血有肉,牛仔裤和女牛仔,挥舞着麦克风的线或走在音符间,直视着我,为我歌唱。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物理 Morrissey,对于他的粉丝——这是 Morrissey 本人。 莫里西说:“我钦佩那些在遭受反复的公开鞭刑、被批评家活活烧死并在他们面前关上许多门之后取得重要艺术里程碑的人。 我喜欢他们到达顶峰时的样子,他们微笑着、克制着、坚定不移。 在我看来,必须珍惜这些例子”。 在那里:多年来我一直珍视莫兹,而今晚,在史诗般的故事之后 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在 黑暗的地下通道 我鼓起勇气,决定把我的身体、我的思想和我的恐惧,以及我拥有的一切都献给他。 为了莫里西,我决定不再住在莫里西。 我决定把它变成一种宗教。
准确地说,恐怕“决定”不是正确的动词。 我毫不费力地承认这一点:我的精神状态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它取消了我的每一个意志,我的每一个想法; 我没有(我没有)工作、家庭、男朋友、爱人或照片可以挂,也没有约会要记住; 我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 我的兄弟,这里唯一值得一提的亲戚,如果只是因为那个臭名昭著的小混蛋能够在我心中激起仇恨,拒绝跟我说话甚至看我,认为我是“无性歇斯底里和智力低下,或者也许是继承权的竞争者,我不知道。 并不是说我很在意:我几乎没看到它,从不离开我的房间,无限期地延长我的青春期,日以继夜地以非常高的音量反复聆听 Smiths 和 Morrissey,用爱滋养自己:“学会爱我, 组装方式……”; 有多少仇恨:“我赞美给你带来痛苦的那一天...“。
仇恨实际上帮助我加强了我的孤独,为我拒绝生活和存在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即使在今天,我也通过它,通过仇恨、鄙视父亲、母亲、孩子、人际关系、爱情、性、众生和所有人类垃圾,从抑郁中恢复过来,当然,只包括莫里西和他的下巴,包括我。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他如此厌恶生命和人性,他为什么不结束呢? 何不优雅告别尘世,颈项绳索,纵身跃入虚空? 首先,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们,在这方面你们没有发言权,我的审判官们,你们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也就是说,我不否认在你存在的过程中,你有时会隐隐约约地感到“孤独”和“绝望”,但孤独是另外一回事,相信我,它是一种可怕而迷人的体验,从中有没有回头路。 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你在这里给我看的那些点,类似于多稳态图:你看着它们,它们看起来像某种东西,然后你闭上眼睛,它们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你更仔细地盯着它们看,它们又变了, 等等, 一直. '无限, 直到迷恋和拖累你 在他们里面,在孤独中,这是一种暧昧的污点。
结束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并非总是如此,而且无论如何它根本不像从外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或明显。 另一方面,你永远不会明白这一切,不是你的感情和你手指上的结婚戒指,不是你的生活。 你相信你是,因此你不是,你永远不会,你从来没有。 你甚至无法毫无感觉地盯着墙壁 没什么,只有墙本身,它在那儿的可怕固定性,无处可去,永远,即使在你和我之后,甚至在莫里西之后。 但我把事情复杂化了一点,最后我不能忘记你们只是办事员,仆人,我捣乱的垃圾桶里的屎,羞辱或摧毁你太容易了, 我的调查官.. 最好回到曼彻斯特,回到 MEN Arena。
所以那场音乐会改变了我的生活。 回到罗马后,我第一次能够离开自己的房间并向世界敞开心扉,尽管只是虚拟的,但我在致力于莫里西的各种互联网网站和论坛中寻找追随者和同谋。 我低估了 Net 的重要性和潜力:在一个月内,我选出了大约 XNUMX 名失败的吉他手和鼓手,并进行了淘汰赛,直到我剩下三个,即 Johnny Marr、Andy Rourke 和 Mike Joyce 的双打,他们是 Net 的其他成员史密斯。 我的 Johnny 比原版高一点,脸上有点疙瘩,但他弹奏的琶音很棒,而且在观众中很上镜; 至于洛克和乔伊斯,他们将留在舞台的后面,在阴凉处,被乐队真正的明星,即我莫里西——或者更确切地说:穿着裙子、黑色长袜和白色拖鞋的莫里西所掩盖。 事情立即开始成形,发展,我没有太多的努力。 约翰尼对罗马的地下场景有一些了解,并设法在 Testaccio 和 Prenestina 之间的潮湿和幽闭恐怖的俱乐部组织了大约十五个晚上。 该小组被称为不守规矩的男孩,来自以下台词: “不守规矩的男孩 / 谁不会长大 / 必须拿在手里”,并全身心投入到史密斯乐队的翻唱中,从舞台上的位置到衣服,再到外观,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他们。
观众分为史密斯的狂热者和漫不经心、有些无聊的观众,但总体上他们都鼓掌,出于同情或出于礼貌。 然而,我并没有在意他们的掌声,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我的表演和约翰尼的吉他演奏。 我恍惚地看着音乐会,就好像我仍然被锁在我的房间里,一个人,被墙壁和莫兹的海报保护着,模仿他温暖而感性的声音或他讽刺的假音,他的姿势。 我既不害羞也不害怕,或者我的审问者——我只是莫里西,即使远离舞台,与约翰尼和其他人的关系。 她们出去泡妞的时候,我就噘着嘴,退到王尔德的作品里,默默鄙视她们。 至于素食主义 ea 肉是谋杀,我碰巧调查了肉店和快餐店,给旁观者一些 食人白痴, 一天晚上,我什至在几分钟后打断了一场音乐会,看着观众并宣布,就像加利福尼亚州的莫里西一样,在 2009 年科切拉音乐节上:“我闻到烧焦的肉味,而且 真心希望是人肉“。
然而,在谈话中,我会想出这样的话:“我总是被和我有同样问题的人所吸引,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时,这也无济于事”,或者:“我总是不得不嘲笑自己:如果我没有发现我作为青少年的社会地位如此荒谬,我会上吊自杀”,或者再次,总是解释莫里西,对试图邀请我共进晚餐的家伙说:“如果你如果我活了五分钟,你就会被触手可及的第一根绳子勒死。” 不用说,约翰尼和其他人都觉得我难以忍受、可恨。 音乐会中断后,安迪和迈克告诉我说我歇斯底里地疯了,我反驳说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史密斯乐队的真正粉丝,因此他们无权听到和演奏他们的作品。 然后我生气地指着迈克,慢慢地补充道:“你恳求和尖叫, 你认为你赢了, 但悲伤最终会降临到你身上……”,让那些有耳可听的人明白——当然不是你们,我的审判官。
然而,那场争吵标志着不守规矩的男孩们结束的开始。 不久之后,一些白痴将我们的表演发布到互联网上,音频失真,镜头抖动,数百名评论员和所谓的 Moz 粉丝开始嘲笑和侮辱我,称我为“无可救药的失败者”,“贻贝”。。 另一方面,我理解他们:他们点击了链接 本篇 魅力 男子 或 I 知道 这是 超过 他们偶然发现了我们的一场悲惨的小型音乐会,而不是史密斯或莫里西的现场表演。 在舞台上我谨慎地模仿他,好吧,但在屏幕上完全是另一回事,真正的 Moz 是无法实现的,我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抑郁无聊的晚上,沉船在互联网上,我的房间和我的生活的精神屠宰场,我什至来侮辱自己的表现,好像要摆脱它一样。 但这些狗屎是谁?,我写了,匿名的,还有很多笑声和其他侮辱,在那一刻,讨厌自己,我决定不再唱歌,除了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像以前一样。 Unruly boys 的经历结束了,我告诉自己,就像 1987 年 Smiths 的经历一样。是时候单独行动了。
安静。 在背景中合唱 每天都像星期天,灯光暗淡,舞台变成灰色。 至此,独白时寂静与部分歌曲的首音交替出现,在轻快、紧迫或忧郁的和弦之间交替 (这个迷人的男人,无处不在,这一夜睁开了我的眼睛) 和葬礼进行曲 (悲伤终究会来)。 女人时而用单调的语气说话,时而振作起来,走在舞台上和舞台上,黑白之间——女演员可以自由移动,为文本赋予身体。 现在,他丢下笔,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翻倒的椅子之间跳舞,将最后一张椅子移到舞台上,拉直并坐下。 有几秒钟,他闭上了眼睛,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总是随着身体的节奏 每天都像星期天, 在狂喜中,随着音乐翱翔; 之后音符逐渐消失,她直起身子环顾四周,就像醒来一样。 一切都很安静。 舞台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介于灰色和黑色之间,但过了一会儿,椅子和桌子再次亮起,白色又回来了。 女人又开始说话了。
Viva Hate 是 Morrissey 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艰难但非常成功的一步,代表作包括 麂皮绒头 e 每天 Is L艾克 S周日, 我的最爱。 许多评论家在与约翰尼·马尔分手后放弃了他,取而代之的是他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单曲并跃居榜首,这是一个神话。 莫兹的力量,因此也是我的力量,在于他纯粹的、永不熄灭的天赋,这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和说,诅咒女王、政客、唱片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 同样,我的审判官们,我可以 我可以 请允许我做我所做的事,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莫里西的名义,以表彰他的才华。 不想再在公共场合唱歌,我不得不尝试别的东西:一种审美的敬意,独特的,一种值得的姿态 麂皮绒头 或 肉类 Is M订单 - 你明白吗?
“Δολοφονία“,准确地说。 我的第一个受害者叫詹皮耶罗·安东尼 (Giampiero Antoni),身高两米,秃顶,留着小胡子,出生于 1958 年,嫁给了奥尔加·安东尼 (Olga Antoni),一个穿着白围裙的胖女人,也是我的第二个受害者,来自巴里或那不勒斯。 他们在拉迪斯波利郊外经营着一家肉店,不断地切牛肉、小牛、牛、鸡等等,不洁恶心。 我不知道食肉动物是否像莫里西和我一样让你们厌恶,我的审判官,但我向你们保证,一个每天将刀刃刺入小鹿或母鸡尸体的人身上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这是一种不人道、残暴的姿态。 莫里西说:“当动物吃人时,我们感到非常不安,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但是,为什么当人吃动物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恐惧呢?”。 另一方面,我向你保证,安东尼夫妇的尸体比他们每天早上切碎和切片的手无寸铁的肉更令人厌恶和恶臭; 就我而言,那些混蛋活该死。 至于描述和血迹,我不太记得在那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什么 卡尼菲奇纳,但我认为我并没有失去理智或惊慌失措,没有,先生,尽管柜台上放着散落的内脏和小牛肉片和鸡肉片。 我一定是摇下了肉店的百叶窗,把尸体拖了回来,拖了地板,保持着外表——想象一下“犯罪现场”吧? 然后我回到家,放了一首莫里西的歌,虽然我不知道是哪首歌,我的审问者。 可能是想休息,想睡觉,所以会偏向 患, 遭受, 小 孩子,暧昧而悲壮的作品,适合午睡和屠杀,视需要而定。 但我不能肯定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反而又杀了人。 那是一个炎热而寂静的夏天,就像西部片一样,空无一人的街道和空荡荡的房屋,我和莫兹无法抗拒诱惑,努力工作了一周,每天。 在第一个受害者之后,事实证明杀死另一个人相对简单,只要没有心理或道德障碍,而我们没有。 在那之前,罗马的屠夫们一直逍遥法外,屠杀了数以千计的鸡和牛而不受惩罚。 几天之内,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处决了其中的六个人,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一种解放。 我会选择合适的肉店,戴上耳机,进去点一磅牛肉, 肉是谋杀 或 死于一己之力,等待最吉祥的时刻,冷静,准备绕过柜台,给背后的混蛋一个惊喜, ZAC, 刺在喉咙里, 扎克扎克,身边的一对, ZAC,胸部的斜线等等,仍然听着莫里西,听从他的声音。 (说着,他拿起笔在半空中挥舞,如刀子一般,然后扔向观众席,扔向黑暗——这时笔不见了。.) 幸运的是,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孤独、脆弱和绝望的女人; 没有人怀疑一个女人,仅此而已。
晚上在家,我又累又迷茫,有时甚至觉得有必要让莫兹闭嘴,静静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和空间,希望能入睡。 可在睡梦中,刀伤和血溅,一次次惊醒,一次次,突然,一遍又一遍,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恐惧,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还好,下午我还在杀戮。 有时,在屠夫和小睡之间,我在楼梯上或厨房里从我哥哥身边经过,莫里西总是在我耳边,但他什么也没注意到,几乎没有看我。 哥哥一直对我冷淡,冷漠,刻薄,无以言表的混蛋。 在我们的父母去世后,顺便说一下,这与这个故事无关,我们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五年,彼此之间从未说过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地内并遵守严格的规则,从禁止吃肉到上厕所、洗衣机、洗碗机、炉灶和电视时间。 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也不爱他。 时间让我们彼此陌生,我想,两个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人,因为早已被遗忘的争吵而互相鄙视。 我添加这些细节是因为它们在稍后的故事中会有一定的分量,我的审判官们——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小狗屎,我就不会在这里。
但是让我们回到尸体。 真正的问题是噪音,身体滴血的尖叫声,已经注定,没有生存的希望,嘴巴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在莫里西和我之间滑过,在耳机里,毁了现场,该死的。 不明白人类为什么欢迎死亡 带着恐惧,因为它使他们摆脱了卑鄙的生活。 除其他外,尖叫声让我造成更深的、反复的、愤怒的、血腥的刺伤,直到他们让他们安静下来,让他们的身体变成一团血和内脏——这就是我在那些该死的图画中看到的:血、内脏、刺伤,仇恨。 唯一逃脱的屠夫,想想看,是所有屠夫中最不吵闹的,也是最后一个。 一击之下,他已经倒在地上,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就像一块死了的石头,不知是不知狡诈,还是晕倒。 我毫不费力地把他拖到后面,确信他已经死了,很高兴我干干净净,和莫里西一起跳舞,和他一起哼着歌。 可惜第二天肉店照常开门,没有警察之类的,肉店是个肌肉发达、有纹身的侏儒,他从窗外打量着我,要我再试一次。 起初我弄湿了——这怎么可能? 我本能地回家了,想也没想,拿起刀又下楼去了肉铺。 我在人行道上站了几分钟,警惕着,我的手在颤抖。 我害怕。 里面有什么在等我? 如果矮人在第一次刺伤中幸存下来,他难道不能在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中幸存下来吗? 有那么多肌肉和纹身,我能杀了他吗? 更多:如果他伏击了我,与其他屠夫结盟怎么办? 当我用这些疑惑折磨自己时,他不断地从柜台后面用侏儒的眼神看着我,剖开一头小牛的内脏,咧嘴笑着,嘲笑我,自信满满,准备为自己辩护,杀人,杀了我。 那一次我没有勇气把莫里西塞进耳朵里。 我不想让他成为我恐惧和投降的帮凶,所以我回到家上床睡觉,盯着天花板直到傍晚才睡着。 我做了一些我不记得的噩梦。
第二天我有点困惑,恐怕。 一开始我想回到屠夫那里,立刻杀了他, ZAC ZAC ZAC,但后来我决定谨慎地离开肉店几天。 我带着耳机离开了家,决定四处走走,最多去参观维拉诺公墓 公墓 G阿泰, 杰作。 但就在我穿过大门,溜进一条满是墓碑和杂草的走廊时, 公墓 G阿泰 结束了,专辑中的下一首曲目开始了,那首血腥的 大嘴巴 S三轮车 A获得“甜美, 甜美, I 是 仅由 开玩笑, ,尤其是 I 说过 ID 喜欢 粉碎 每周 牙齿 in 选择您 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几岁的中国人,一个皮包骨头的小男孩,手里拿着鲜花。 他想把它们卖给我,送给我,得到一些零钱,装饰我的生活。 他的尸体应该还在坟墓和杂草丛中,我的审判官,虽然这一次这个想法困扰着我,因为我不应该杀了他。 莫里西 是不是 确实是种族主义者。 暧昧的诗句 孟加拉语 P平台 – “Oh, 搁置 选择您 西式 计划 和 理解 / 这 生活 is 硬 更多 ,尤其是 您 属于 此处= – 更多地针对英格兰的苦难而不是孟加拉人,无论如何,它们都包含在专辑 Viva Hate, viva l'odio 中,因此在我看来是必要的。 顺便定义 国民阵线迪斯科 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就像 NME 当时所做的那样,简直是愚蠢的; 这是关于 艺术, 而这首歌的法西斯只是一个 穆萨,如在 甜 温柔流氓. 另一方面,莫里西结束了关于他在专辑中涉嫌种族主义的谈话 完全 A重新 Q猎物, 从 2004 年开始:“我一直梦想着成为英国人不再是平庸的时代, 站在国旗前不觉得丢人, 种族主义或部分……”。 也确实,此后不久他会把中国人定义为一个 亚种,但在采访中,Moz 始终是 Moz,无论如何,这些人对待动物就像对待野兽一样,我的调查官,这是他们应得的。
无论如何,不管是不是亚种,我都不应该屠杀那个孩子,莫里西不会同意的。 我茫然地离开墓地,流着汗,倾听着 恐慌 告诉我我犯了一个错误,犯罪,我不能回去。 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悔过 真 某种东西,做出一个可怕的、无法挽回的手势,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同样的瞬间,同样的恐怖,一个孩子撕裂的、浸透鲜血的喉咙,以及他喉咙里发出的、可怕的、永恒的哭号。 我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但还是第一次 我感觉到了什么,这太可怕了。 我再次穿过城市,想尽快结束它,迎合地铁的狂风,跌倒在铁轨之间,火车下,让自己不知所措。
但我没有,莫里西一点一点地战胜了他,救了我,把我拖走了,用他的声音,甚至原谅了我——”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I 确切地知道它们是什么……”——也许是在赞美我,毕竟那个中国男孩是他的牺牲品。 我到达我的宫殿时仍然大汗淋漓,但平静多了。 我逃脱了。 杀死那个小男孩是残忍的,好吧,但莫兹负担得起一切,我和他一起。 我进了电梯狂野的步伐 野蛮行为始于家庭,在镜子前跳舞,我走到我的楼层,打开门,突然我遇到了我的邻居,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一个退休的法官或律师,从不出去。 他久久凝视着我的眼睛,仿佛 知道,谴责我,然后我再次上前杀人,”哦,你这个英俊的恶魔”。 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我的审问者,就好像我下错了电梯——“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我下错了电梯”:莫里西在 1987 年,关于他的生活——突然我发现自己和尸体在一起一个老人在他的怀里,在房子前面。
我把它带进去了; 我还能做什么? 我把他拖到走廊上,把他靠在沙发上,坐起来,双腿伸直放在地板上。 他的头左右摇晃,软弱无力,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而不是一具尸体。 我仰起他的头,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两只睁大而呆滞的眼睛,这一刻,想起他刚才指责的眼神,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悔恨和无可挽回的感觉,就像那个中国男孩一样。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是,两人都没有为活命做过什么,让刀子左右切开他的喉咙和腹部,没有挣扎。 有时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错,受害者,好像 他们想 被杀,利用和迷惑我们,我的审判官。
然而,我却久久地躺在地上,莫里西的惨叫声在我耳边响起,倒在血泊之中,仿佛在注视着这个老人。 我心碎了,筋疲力尽。 当我看到走廊里的灯亮着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惊讶地发现外面已经是晚上了,莫里西已经不在唱歌了,当我哥哥朝客厅里看了看,发出了一声惊呼。我惊恐的叫了一声,没有说话,移开了视线。 他走过去,靠在老人身上,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肩膀靠在沙发上,昂着头,鲜血四溅。 “但他是……邻居,”她说。 “是邻居! 什么——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那不是很明显吗? 我哥哥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尸体上,反之亦然,不理解,就像他对我和我的生活,我的审美一无所知,继续按住那个他几乎不认识的肮脏老人的额头。 然而,多亏了那个手势,我突然对他有了某种感觉,一种温柔。 “什么——他怎么了?” 他重复了一遍,徒劳地试图让老人复活,但他却对我说,对他妹妹说。 一瞬间我意识到 可以要他 好我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有那么长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刻,我意识到血液意味着某种意义,不止一种,我和我哥哥都搞错了,毁了我们的生活。
他在大喊,“他没有动,他死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到了那个“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多年来没有和我说话——为什么? 或者是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但为什么,又一次? 突然间,每一种人际关系对我来说都显得悲惨而可怕,我跳了起来,好像在反叛,现在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大喊大叫,而我跳到他身上刺他的胸膛,刺他的心;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大喊:“住手,阿米莉亚! 停止! 是我!”,如果他感到爱、恨、困惑、恐惧——或者如果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就像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一样。
我。 他,停下来,阿米莉亚,停下来。 Amelia,我的调查官。 人际关系是悲惨和可怕的,但除了音乐和恐怖、孤独和白墙之外,别无其他。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现在我浪费了我的生命。 当我哥哥停止喊我的名字时,我也停止了。 一切都静悄悄的。 把灯关掉 (舞台上的灯光也相继熄灭, 伴随着他的声音; 阿米莉亚倒在椅子之间, 在昏暗的灯光下) 然后蹲在尸体中间,在血泊中,试图死去,一动不动,也没有呼吸。 但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另一方面,Morrissey 还活着,所以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能结束它,还不能——不能在他还活着唱歌的时候结束。 我将不得不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在这些黑墙之间,黑暗,就像你周围的世界,就像我的话一样。 我会继续生活和仇恨。 可怜我吧。
窗帘.
住在莫里西身边
笔者
Edoardo Pisani 1988 年出生于戈里齐亚,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乔内和罗马居住。 他为一些杂志翻译和编辑文本,并在 2011 年被选为曼图亚音乐节的 Scritture Giove。 目前他在罗马写作和工作,他用 goWare 出版了这本小册子 呕吐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