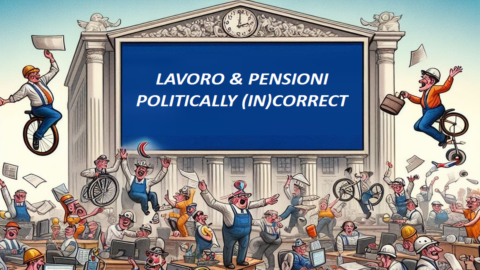关于一个问号
是西德尼·韦伯吗?——?伦敦经济学院的联合创始人、费边社的推动者和工党的创始思想家之一?——?谁从他的 1941 年第二版著作中去掉了问号苏联(与妻子比阿特丽斯合着)苏联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 (1935 年,1950 年意大利版 Einaudi)。 换句话说,问题已经结束:苏维埃俄罗斯是一个新文明。
我们正处于斯大林时代的中期,伴随着莫斯科审判、大规模驱逐以及 1929 年至 1933 年富农的灭绝。 Sergej Kropacev 和 Evgenij Krinko 最近的一项研究,1937 年至 1945 年苏联人口的减少:实体、形式、史学(由 Francesca Volpi 意大利语翻译,goWare 出版商)得出以下结论:从 1929 年到 1953 年,不包括年份在战争中,镇压的受害者有 19,5 万至 22 万,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被判枪决或死于集中营和流放。
就像葛兰西所说的“从定义上来说,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是浪漫的”,这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民主的危机,或者是由于改革派政党的失败,事实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最终屈服于苏维埃俄罗斯的神话。
苏联的光辉形象和苏联神话滋养了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整整几代人。 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保留在他家壁炉上的几张照片中,有一幅是斯大林的肖像,左边是列宁的肖像。 Judging Shaw 的作者芬坦·奥图尔 (Fintan O'Toole) 讲述了爱尔兰知识分子对斯大林的迷恋,斯大林将怀疑主义作为其世界观的基础。 与俄罗斯媒体和克里姆林宫不同,纽约报纸通过在报纸的专栏区设立一个名为“红色世纪”的特殊空间,为这一周年纪念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欢迎数十篇文章和俄罗斯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学者和专家的贡献。
回到基础研究
在这里,马塞洛·弗洛雷斯 (Marcello Flores) 的一本书《苏维埃俄罗斯的形象》也终于面向历史和政治爱好者的大众开放。 列宁和斯大林的西方和苏联(1917-1956),p。 550,18,99 欧元(电子书 9,99),goWare 出版商。 这是一本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该过程通过大量文献分析了西方人的眼睛如何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俄罗斯的现实来衡量自己。
而之所以新出版《苏维埃俄罗斯的形象》,恰恰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很少,所以在第一百次之际重新提出它仍然有用。俄国革命纪念日。 对俄国革命、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研究在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即自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和苏联解体以来:史学已经完全更新,易于理解文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成倍增加,证词被重复,并且在共产主义年代隐藏和审查的大部分作品已经公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排除一些出色但孤立的贡献(Sophie Coeuré,Sophie Coeuré, La grande lueur à l'Est: Les Français et l'Union sovietique, Seuil, Paris, 1999; Sophie Coeuré and Rachel Mazuy, Cousu de fil rouge. Voyages des intellectuels en Unione Sovietiques, CNRS, 巴黎, 2012; Michael David- Fox, 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Cultural Diplomacy &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2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2). 幸运的是,Marcello Flores 这本书又回来了,我们为您提供介绍。
一个持久的神话......他的?尽管
苏联,对这个国家的兴趣非常有限。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它几乎成为大众媒体每天关注的对象,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历史留下的活力彻底扭转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
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研究的结果,最初旨在审视美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苏联的形象,然后扩展到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这一更广泛的主题列宁和斯大林。 确实,正是在格鲁吉亚独裁者形象主导的近三十年里,西方创造了苏联神话,在 1956 世纪 XNUMX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在 XNUMX 年跌宕起伏后找到了最后的时刻. 显然,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人造卫星和 Jurij Gagarin 的太空探索在全世界发挥的魅力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已经走下坡路的神话,已经耗尽了它的资源,无法自我更新。 尽管与俄国革命的消息几乎同时在西方传播的十月神话有部分联系,但列宁和斯大林的俄国神话是一个新事实:就其所呈现的特征而言,也就其传播范围而言,它涉及的社会群体。
两党神话
正如从一开始就清楚的那样,民主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享有特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这些国家设法幸存下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允许所有政治倾向?——?从革命到反动,从激进到保守?——?根据苏联的经验来衡量自己,而不会被窒息,只受制于他们自己和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
当然,民主在其他地方也幸存下来,但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最大,苏联问题的连续性和邻近性最为明显,苏联更关心这些国家的判断和态度。
试图尽可能地给意大利和德国留出空间,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经历无法与民主国家相提并论。 墨索里尼政权对苏联的兴趣,尤其是对左翼边缘的关注,反映在工业界的态度以及在苏联的意大利游客的种类和数量上。
至于德国,最重要的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世界开始与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作斗争,正如纳粹胜利后写的数十篇旅行故事所证明的那样,许多稀有。 苏联在接纳大量反纳粹德国难民方面的作用已经被提及,但它显然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构成了不同的问题。
完整的壁画
我的重建所依据的材料本可以以更具分析性和更详细的方式使用。 我是第一个意识到本书的每一章,有时甚至是每一段,都应该成为独立研究的主题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
然而,在我看来,提供合成的因此必然更不完整的图片的可能性似乎是一个更有趣的选择。 至于没有使用口头资料,原因很简单:我对史学的这个重要分支及其最初提供的方法论技巧不熟悉; 还有追查他们的困难,重温故事的模棱两可,书中大多数主角的失踪。
因此,我更喜欢使用同质来源,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形象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公开和历史上的有效变化上。 因此,对个人故事和个人心理的关注都指向了这一优先兴趣。
当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使用所有收集到的材料,或者没有使用其应有的广度,尤其是在处理旅行者等第一手证词时。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壁画的选择不利于非常丰富且不幸的是经常被遗忘和低估的来源的价值。 那些对读者来说只不过是参考书目中的名字的人物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知识、反思和比较来源。
很明显,一些证人由于他们的取向、敏感性和他们表达的判断而比其他人更接近我。 这些是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角色,并不总是归因于一个政治或文化人物。 对他们的同情并没有阻止我也使用其他人,他们同样拥有丰富的信息和建议,而没有将他们扁平化为由今天的史学或当时的判断预先包装好的陈词滥调。 你在本书过程中遇到的所有角色对我来说都是问题、答案、需求和真实态度的载体。 毕竟,在不止一个案例中,我评估、判断、评价和背景化各个人物的方式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我希望读者,即使他不来分享我的论点,也能在我收集的材料中找到足够的内容来支持他的信念,并可能对它们提出质疑。
历史,一个无限的谜题
我从来没有像在这种情况下那样说服自己,历史是一种无限的谜题,它本身包含多种可能性,都是部分的和不完整的。 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尽可能全面、全球和连贯的观点,使今天的需求、问题和敏感性与所研究时代的复杂现实相协调。 不断参考那个时代的背景,并不是一种避免判断或不表明立场的方式,它是一种尝试吗?——?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以保证自己不会扁平化已经结束的和曾经有过的经历它自己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
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我的目标是展示西方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广度、深度、清晰度和矛盾。 特权过滤器是知识分子的过滤器,文化世界的过滤器,无疑是扩大感知和传播苏联形象的最重要载体之一。 因此,作家、记者、艺术家与工程师、医生、技术人员、外交官和政治家一样,代表着特权来源。 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给直接叙述以最大的空间,大量使用?——?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过度?——?引用。
考虑到放置它们的上下文的选择足以保护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这不是一种隐藏在来源后面的方法。 相反,这是一项累人的、漫长的、有时是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不得不取消、减半、忘记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感兴趣的文本。 我希望属于那个时代气候的那种悲惨和粗俗、绝望和天真、愤世嫉俗和敏锐的感觉能够保留下来。 从来没有声称让来源和人物为自己说话,我试图将我的干预限制在选择、联系、选择和语境化上。 我重建的绝对主角不是解释,而是现实; 这个世界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发现了一个鲜明而重要的反映,足以值得研究。
Marcello Flores 在的里雅斯特大学(1975-1992 年)和锡耶纳大学(1994-2016 年)教授当代史、比较史和人权史,是华沙大使馆的文化专员(1992-1994 年),目前是科学主任米兰 Ferruccio Parri 国立研究所。